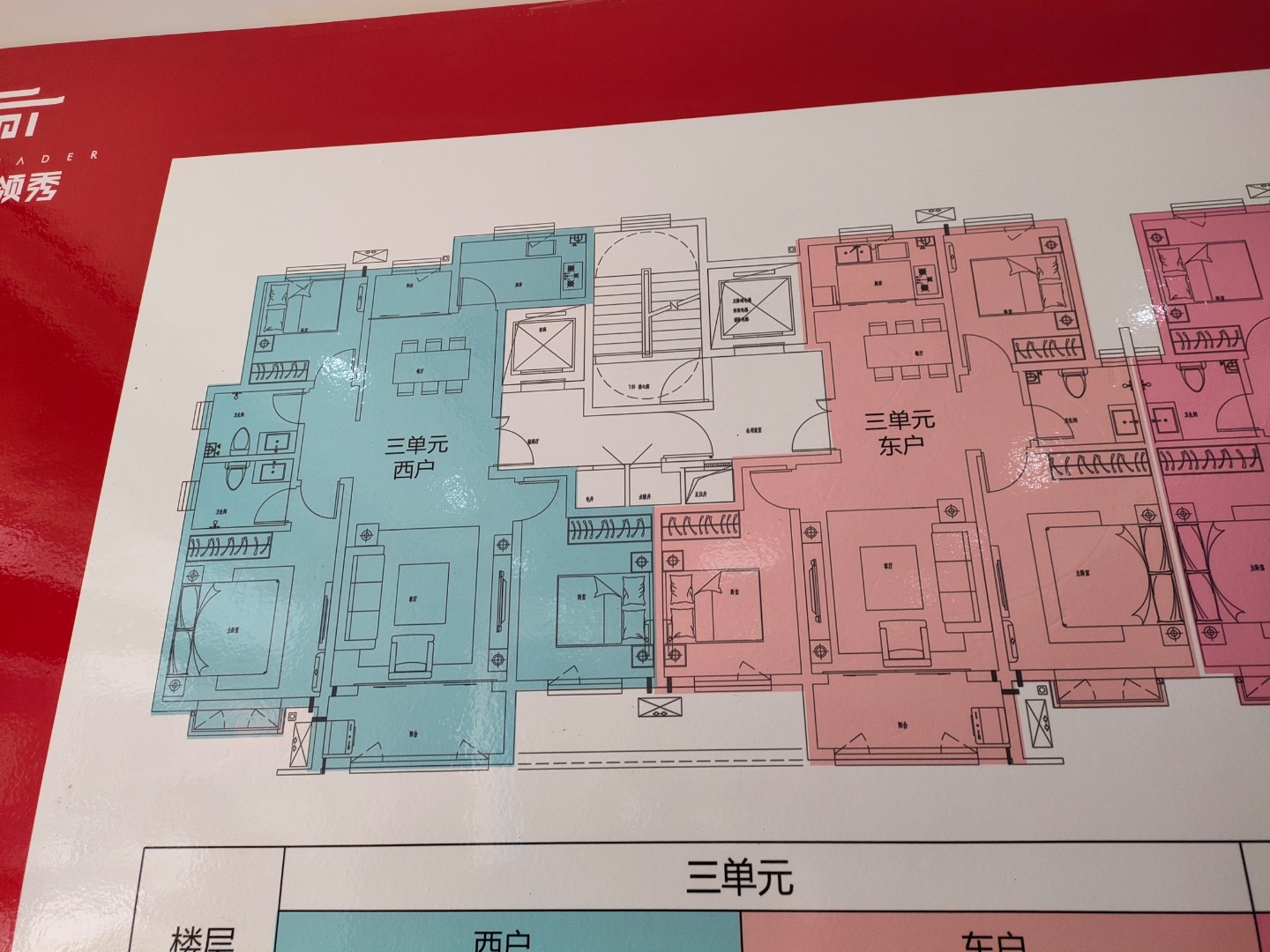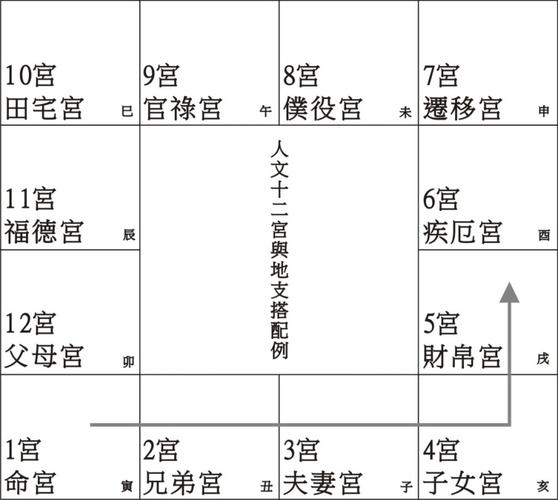自然法思想的理论渊源及托马斯·阿奎那伦理自然法与道德价值的关系
自然法思想的理论渊源及托马斯·阿奎那伦理自然法与道德价值的关系
自然法( law)在西方文明的观念中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如果没有自然法,罗马法绝不可能演变成为后来国际文明的普遍法律;没有自然法,也不会有美国与法国大革命。自然法观念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是法律与道德哲学一笔持久不坠的遗产,其重要性可以说超越了人们藉以说明它的时空因素。自然法思想所引发的对人权、正义、自由、道德的关注影响深远。自然法理论是托马斯·阿奎那( ,约1224-1227)伦理学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本文在追寻自然法的理论渊源的基础上,旨在揭示托马斯的“伦理自然法”与道德价值之间的关系及其思想实质。
一
自然法思想在西方历史上源远流长。古希腊思想家最早使用“自然法”这个术语,并确定了自然法的基调或方法论。在古希腊思想家看来,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则和秩序的,不仅自然界存在着规则,社会之间、民族之间、个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有它们先前已经确立的秩序。这个秩序就叫做“自然法”。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就试图发现支配宇宙的自然法,之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都确信存在着实在法的某些不变标准,并断言,通过理性的运用,可以发现这些不变的标准。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正义有两种:一种是自然正义,一种是约定正义。自然正义在任何地方都有相同的效力,比如火在希腊和波斯都是以同样的方式燃烧的;而约定的正义则纯粹基于规定,如赎金数量的多少等。从中不难看出,古希腊的自然法与自然法则基本相通,并没有抽象的道德内涵。自然法作为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以及以此建构的学说,肇始于斯多葛学派(Stoic )。
斯多葛学派创始人芝诺(Zenon)及其追随者把“自然”作为要领置于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心。斯多葛学派哲学以伦理学为中心,依其发展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早期学者主张人应当顺应自然,遵循理性与道德来生活,亦即惟有合乎理性的行为才能使人类幸福。中期学者将伦理学融入古罗马社会,强调理性是为了向人类指明道德,而道德就是个人对国家的义务。晚期学者则对人生抱以悲观的看法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将人的肉体视为精神的坟墓,认为人的一生是有罪的、痛苦的,惟有忍耐和克制欲望,过着自然的生活,才能得以解脱并获得幸福。整体看来,司多哥学派学说的基本概念就是“顺应自然”。依据对大自然朴素的、直观的观察,斯多葛学派的学者认为,人类的自然本性是宇宙本性的一部分,宇宙的本性就是理性,宇宙的规律及必然性就是理性的规律及必然性。亦即理性就是自然。人类服从以理性为基础、具有普遍性质的自然法,就是服从宇宙中不能改变的规律及必然性。不过,他们所说的“自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界,而是某种和谐的秩序;不仅是事物的秩序,也是人的理性。人的理性是自然的一部分,理性支配宇宙,人作为宇宙的一部分也受理性的支配。理性是适用于所有的人并使所有的人能够平等地、协调地生活在一起的支配原则。因此,按照理性去生活,就是自然地生活。自然法就是普遍存在和至高无上的法则,它构成了现实法和正义的基础,它的效力远远超过人类领袖所制定的法律。因此,人类所制定的法律应该符合那代表理性、统领世界万物、永恒不变的自然法。由于自然法的效力遍及世界万物,所以,其命令就代表着客观、公正,人应该一律平等。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受两种法律的管理:一是自己国家的法律(习惯法);一是这个世界的法律(理性法),而二者之中以理性法的权威性较高,它是各个国家所遵守的法律规范,各个国家的习惯虽有不同,但人类的理性却只有一个。
斯多葛学派关于自然法的主张对古罗马法学及中世纪经院哲学( )的影响是极其深远。古罗马时期的自然法思想受到斯多葛学派卡里西巴斯()的影响很大,卡里西巴斯在其《论法律》一书中认为,法律是上帝及人们所有行为的统治者,它分辩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的标准,对一切有理性的社会动物而言,法律是指示他们什么事必须做,以及什么事不应该做的指针。古罗马人一开始只订出他们自己的法律,而后观察到一切的法律都有共同点,并且渐渐认识到法律的基础为自然理性。之后,他们进一步观察发现,在一般法律之外还有一种永久的法律存在:“自然法乃基于人类共识的自然理性。”[1]西塞罗()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的思想,倾向于将自然与理性划上等号,认为理性是宇宙规律的力量。西塞罗指出,“法”是一种自然权力,是人的理性,是人衡量正义与不正义的标准;“法”是最高的理性,它深植于支配该做及不该做的行为的自然中,当理性稳定和充分发展时,就成为“法”[2]西塞罗还以自然法说明人类理性、正义和法律的关系。他认为,上帝赋予人理性,没有任何事物比理性更为美好,因为理性存在于人和上帝两者之内,所以,人和上帝第一份共同财富就是理性,正当的理性就是法律,共享法律的人也必共享正义。西塞罗认为自然法不能废除,因为它是正义的本源,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中世纪之前,自然法观念在古希腊哲学中首先表现出深刻的自然主义()特征,而后发展出正义、平等的哲学理念,为托马斯·阿奎那伦理自然法思想提供了深厚的理论铺垫。古希腊人以朴素的、直观的视点和方法来考察法律现象,从而认为,最初的国家和法律,就跟江河湖海、山川草木、飞禽走兽一样,统统属于大自然现象,即自然形成的。所以,对国家和法律,要把它们当作自然现象的一部分或者在大自然的延长线上来加以把握。希腊城邦通行的伦理美德、风俗习惯、对神灵的信仰、法律等都要放在自然主义中理解。在他们看来,人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自然是不可侵犯的。希腊哲学与罗马哲学将法区分为自然法与人定法,这种法的二元论是自然法哲学最根深蒂固的思想渊源,只承认人定法,自然法哲学就无从谈起。希腊哲人提示出自然法的本质是正确的理性。人区别于自然界其它动物的特征在于人具有理性,理性使人结合成全社会。因此,理性法就是自然法。理性的力量在于它规定什么是正确的、善的,什么是错误的、恶的。人类必须遵循理性的命令,制定具体的法律,“法”是根据于自然的最高理性,它规定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事不应该做。当这种理性的人类的思维中确立下来,它就是法律。因此,自然法是正义的基础,只有是正义的才是善的和理性的,正确的理性指明了善与恶,规定了正当的行为与非正当的原则界限,因而为正义奠定了基础,作为人类行为规则的法律必须体现正义即正确的理性,非正义的法律是无效的,所以,不符合自然法的人定法是无效的,自然法是唯一绝对有效的法,任何人定法都不可能使自然法失败。而违反了自然法,即使具有法律形式自然法思想的理论渊源及托马斯·阿奎那伦理自然法与道德价值的关系,也是无效的。由此,斯多葛学派主张一切人都是平等的,即使人们的地位、天赋和财富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别,但人人至少都有要求维护人的尊严的起码权利,正义要求法律应当认可这些权利并保护这些权利。这种认识和观念构成了西方法律传统活力的基因。
二
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关于“法”这一概念的详细论述见于其著名的论著《神学大全》(Summa )第二部[3]。阿奎那认为,“法是由管理社会的人,为公益而制订和颁布的理性()命令。”[4]阿奎那将法分成“永恒法( Law)”、“自然法”及“人定法(Human law)”。所谓“永恒法”,按照阿奎那,即“上帝掌管万物的理性[5]”,或是“上帝指导万物一切行为和活动的计划” [6]的,上帝不在时间之内,故为永恒法。“永恒法”是人类必须永远遵循的最高样式。人类依循“永恒法”的途径有两种:第一是以获得知识的方式分享“永恒法”。另一种借由行为和喜好的方式,以内在动力的原则去分享“永恒法”。理性受造物自然倾向于拥有“永恒法”的知识,以成为具有德性之人。统治人民的君主和法律的制定者则必须依据上帝智慧做出正确的判决,亦即所有法律必须由“永恒法”出发。
上帝创造了大自然,自然法来自于永恒法,永恒法则存在于创造者的智慧中。因此,托马斯以“上帝所赐规则”来定义自然法。在托马斯看来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所谓“自然法”,即“理性受造物所分享的永恒法”[7]。整个宇宙与人类社会均由上帝所分受,而理性受造物由永恒法中所分受的,则称为自然法。人定法被理解为用强制手段来制止人们作恶的国家的法律和法规的总称。托马斯确地提出自然法作为国家法律的标准,这些标准同时建构出权利和道德责任的基础,亦即托马斯建构自然法,作为人类活动正确指引,并提升至人类社会中。
托马斯伦理学的重点,可用两个基本概念去理解,一是‘律’,一是‘自由’。‘律’的问题,首先是自然律(lex )……”[8]上帝创造了自然,自然法来自于永恒法,永恒法则存在于创造者的智慧中。因此,托马斯以“上帝所赐规则”来定义自然法。整个宇宙与人类社会均由上帝所分受,而理性受造物由永恒法中所分受的,则称为“自然法”。在托马斯这里,因为“法”是“理性的”命令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自然法思想的理论渊源及托马斯·阿奎那伦理自然法与道德价值的关系,而那些无理性的受造物既无理性,则无法认识,也不能给自己宣布任何自然法。但是,人却能做到。因此,“自然法”一词,不是用来称呼人的理性所反省的人生的自然趋势和倾向,只是用来称呼人的理性所宣布的反省的结果,亦即理性藉此而颁示的命令。从这个意义上讲,托马斯所讲的“自然法”更确切来说就是人的“自然道德律”( Moral Law)。自然道德律泛指正当理性关于应行之善及应避之恶所颁布的普遍诫命。[9]
阿奎那的自然法是神学自然法。上帝是万物的主宰。被统治的涵义之一是参与统治者的法则。因此,万物参与永恒法,按各自的本性朝一定目的运作。理性动物以其理性之光(the light of )参与永恒法。在阿奎那这里,自然法派生于永恒法,自然法就是永恒法的一部分,这就是自然法的本质。阿奎那的理论根据是:上帝创造人而规定人的本性时,实质上就是给人的心中印下了部分的永恒法。“这部分的永恒法就是自然法。所以,自然法已经印在人的心中,而且无法磨灭”[10]正因为如此,人一生下来,就受到自然法的管制。虽然,人无法在上帝的理智内读到永恒法,但人可以认出自己本性内的基本倾向和需要;在反省这些倾向和需要时,他就能认识人性所固有的自然道德律(自然法)。人都有发展自身潜能的自然倾向,以得到应有的善。人也都有理性之光,藉此而反省自己本性的各种基本倾向,而给自己宣布自然道德律——正当理性关于应行之善及应避之恶所颁布的普遍诫命。
自然法的首要诫命为“趋善避恶”,一切其它原则皆由此导出。[11]自然法的三条基本原则是:第一,自我保存——“每一实体(包括人),都各按自己的种类,倾向于保存自己的存在”;第二,性生活,养育后代——“人与其它动物所共有的生殖传统的本性倾向”;第三,追求真理及过社会生活——“人有一种自然的倾向,去认识有关上帝的真理,以及过社会的生活”[12]。所以,自然道德律从整体看来,在于许多普遍程度不同的诫命;不过,这些诫命同时又都被包括在“当行善避恶”这条基本诫命里。[13]
人定法源于自然法,凡违背自然法的法律皆不成其为法律。自然法是通过两种形式成为人定法的基础:第一,由自然法原则演绎成人定法条文,此类法律具有自然法的效力。人类的自然倾向是过社会生活,不做有害他人的事情。一般人可以通过接受教育而约束有害他人的欲望。但有的人却不接受教化,不可理喻,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惩罚和习惯约束自我。[14]阿奎那认为,立法优于人治。因为:首先,找到少数称职的立法者比找到大批称职的裁判官要容易;其次,立法者有从容时间研讨,而裁判官却需要当机立断因而容易发生判断错误;第三,立法者概括原则并作长远考虑,裁判官就事论事因而易受到眼前利益或情绪影响。[15] 由于人定法源于自然法,因此,公正的法律对良心具有约束力。换言之,不公正的法律对人民的良心可以不具有约束力,人民有权推翻这种不公正的法律及维护这种法律的暴君。[16]
三
从托马斯的伦理自然法理论中看出,伦理自然法与道德价值存在着内在的关系。一般来讲,人生价值分为物质的、精神的、伦理的三种。人在衣、食、住、行各方面所需皆离不开物质,就连人的身体本身也是物质的。因此,人需要物质价值是无可否认的。在物质价值之下,人也需要精神价值,因为,人有区别于普通动物的精神的理智,因此,人需要文学、美术、音乐、科学等等各种文化。实际上,人的精神价值甚至比物质价值还要重要,正如约翰·密尔(J•S•Mill,1806-1873)所说:“与其做一个满足的猪,不如做一个不满足的人;与其做一个满足的傻瓜,不如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17]
按照托马斯·阿奎那,除了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实际上,人还需要伦理价值或道德价值,因为,人有人格,道德价值就是人格价值。物质价值无论有多么重要,都不可能成为人的一部分。精神价值虽然是发展人的天赋,增加人的知识,真正的变成人的一部分,精神价值毕竟还未触及人格,没有塑造人的德性,没有完成真正的人生目的。道德价值是人以自己的自由能力,使理智与意志发展到完善的境界,完全与真、善、美相符合,这是发展主体,而又归于主体,最后完成主体的最内在及最高尚的价值。
道德价值如何建立?其基础何在?根据托马斯的伦理自然法理论可知,伦理自然法就是做人的自然法,就如同一物所以为其物,必有为其物的自然法,没有物违反它的自然法而可以存在,鱼不能离开水而生活在陆地上,猫儿不能离开陆地而生活在水中。人不依照伦理自然法生活固然不会致死,但是,人那样做的结果,按照托马斯,人就会与无灵之物无异,也就不能完成其人格,其精神生活必趋向死亡。人不能违反自然法,因为自然法是人的“本性()之律”,它注定了人生存与活动的规律。
既然自然法来自人性,那么,是否人性就是道德价值的基础呢?按照托马斯,并非人的所有行为都是道德行为,都有道德价值可言,人的生理活动,如血液的循环,心脏的跳动等,就没有道德价值。因为它们是生理的自然能力,不是有意志的行为。意志虽然有选择善的自由,但并非所有由人完成的行为都是道德的行为。所谓道德行为,只能适用于发自理智和意志(即理性能力)的行为,托马斯称其为“人性行为”[18]。也就是说,一个有道德价值的道德实践,按照托马斯,当是“正当的理性”加上“向善的意志”方可达致。
在西方自然法观念的演化中,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法学说富于创造性,而且自成体系。概括起来,这种自然法学说的特征,主要有如下几点:
1.与古代自然法相比,自然已不再是最高的法。“自然法是理性动物对永恒法的参与”,这就是说,自然法成为人定法通向永恒法的桥梁;自然法是道德准则的来源,是永恒法在人身上的体现,是人类理性制订具体的道德准则的依据。同时,自然法还是宗教戒律(神法)和教会与国家法律(人类律法)的来源与依据。这表明,上帝(永恒法)参与人的道德生活无所不在。A·拉斯卡认为:“上帝的存在,从结构意义上来说,对于阿奎那的自然法理论阐述并非一个相关的、也不是一个必要的概念和条件”。[19]这一评论显然过分看重了自然的维度,同时忽视了恩典对于自然所具的主导性意义,是对阿奎那苦心经营的调和体系的曲解。如果说恩典并不废止自然,自然当然更不会废止恩典。理性固然与信仰携手并进,但理性终究只是恩典的侍女。在阿奎那的理论中自然不过是最终用以达到恩典这一更高目的工具。自然法只是做了人类向神恩之永恒至福攀登的一个阶梯。上帝当然是宇宙和神圣的永恒秩序的牢固终端。
2.从内容上,自然法肯定了人的独立存在的地位、人的尊严、能力以及人的实践理性所享有的自律和自主。在以往的、尤其古希腊人的自然法理论中,人的独立地位到极大的漠视,人自身的属性几乎是消逝了。阿奎那的自然法学说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它把人的本性作为自然法的基本规定,认为:“自然法是与人的本性相符相称的东西”[20]。虽然,阿奎那的伦理体系并不能绝对地称为理性主义体系,因为其中还欠缺近代理性主义那种自高自大的精神。它并未主张人是自足的,并未主张人本来就完美,它并未坚持诸般抽象“权利”,并未视个体为一切法律与一切准则之终极根源而坚持其自主性。因为在阿奎那的自然和宇宙当中,弥漫着由上帝之神圣理性创设的永恒秩序,在这一理性秩序当中,宇宙万物,从无生命的东西一直到有理性的人,都被安排了各自适当的位置,被赋予了各自所应努力加以实现的本质,就连上帝自己也应服从这种神圣的永恒秩序,上帝不能否定自己。它要求从宇宙出发,从一个秩序井然、等级分明的世界的观念出发看待万物、规范万物,而不是从个体出发。自然法不过是理性造物对这种宇宙理性秩序的一种参与罢了。它强调的是法规而非权利,是对国家的义务而非个体的权利,最终,一切皆源于永恒不变的理性秩序。同时,应当看到,在阿奎那的伦理体系当中,保全人的生命、维持人的各种本能和维持社会生活秩序是与自然的倾向和上帝的意愿相一致的。阿奎那认为,在所有受造物当中,人因禀有理性而成为唯一受命参与宇宙理性者。这是对人的尊严和能力的肯定。尽管人堕落了,但他并未丧失正确运用自己力量从而为拯救自己作准备的努力。人的贡献不但需要,而且确实不可缺少。阿奎那的自然法理论,正如A·P·登特路夫所言“象征着人类价值与基督教价值之基本和谐,象征着人达到完美境地的可能性,以及他的理性的力量与尊严和他的理性。”[21]在阿奎那这里,永恒法之与自然法,为自然法之永恒而超越的基础;但人之接受自然法,并非只视之为一种由上而来的命令,人事实上能够认出这自然道德律本身所有合理处和约束力,从而将它向自己宣布出来。换言之,作为道德客观标准或外在原理的自然法,一方面反映或分享着永恒法,;另一方面,从它直接由人的理性所宣布这方面来讲,又显示人的实践理性享有某种自律或自主。[22]
总之,在西方自然法观念的演化中,阿奎那的自然法思想可以说是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虽然,阿奎那的“这个学说有不少逻辑困难。自然的有序性与人类的行为规范并不属于同一意义层面。而且,自然中的秩序并不一致,师法羊的和平驯顺,抑或师法虎狼的弱肉强食,亦难以一致。”[23]应当看到,阿奎那的自然法是以自然法为人类理性对永恒法的参与。永恒法使人类具有按终极极目的而发展其潜能的天然倾向;理性对这种天然倾向进行自省思辨而颁发的道德律令就是自然法。也就是说,自然法并非自然法则本身,也非神启,而是实践理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律令。阿奎那自然法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确立自然法的新意义结构,排除师法自然规律之说,而以理性颁发的普遍律令为自然法,这也就是要赋予自然法以终极意义、普遍性和一致性。只要承认终极目的和人类现有理性,则须承认每个人有自我生存、养育后代、在公义社会生活中追求知识和幸福(永福)的权利。个人是自主的目的而非手段。但万物都是受造物。自此,近代自然法理论大致以理性内省为法的来源,“亦即以正常理性经自省而认肯者为自然法。” 从而呈现出“理性主义”、“个人主义”、“激进主义”、“分权主义”和“社会契约论”的特征,对近现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注释】
[1] 详见于米拉格利亚,《比较法哲学》,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301-303页。
[2] 详见于西塞罗,《法律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4-77页。
[3] St. , Summa ,I-II,QQ.90-100, pp.933-1036.
[4] St. , Summa ,I-II,90,4. “…the of law may be ; and it is else than an of for the good, made by him who has care of the , and .”
[5] 人类的一种自然的能力,是行为或信仰的正当理由,评判善恶是非的根本标准。
[6] St. , Summa ,I-II, 91,1; 93,1.
[7] St. , Summa ,I-II, 91, 2.“It is that the law is else than the ’s of the law.”
[8] 邬昆如:《伦理学》,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3,页43。在此,“律”即“法”。
[9] St. , Summa ,I-II,91,2.
[10] St. , Summa ,I-II,94,6.
[11] St. , Summa ,I-II,94,2.“Hence this is the first of law that good is to be done and , and evil is to be . All other of the law are based upon this……”
[12] St. , Summa ,I-II,94,2.
[13] 值得注意的是,阿奎那并不认为我们有人去做一切可能做的善行的道德义务,只有去做那些不做便有罪的善行的责任。因此,必须做的行为,是道德行为(或善行)之一。
[14] St. , Summa ,I-II,94,1.
[15] St. , Summa ,I-II,95,1-2.
[16] St. , Summa ,I-II,96,4.
[17] J•S•Mill, , by Khomo. The Press,p.9.
[18] St. , St. , Summa , I-II,1.1.
[19] A. : ’s of Law: An , Press, , 1996, p.120。
[20] St. , Summa ,I-II,94,2.
[21] A. P. 登特路夫:《自然法—法哲学导论》,李日章译﹐台北﹕联经, 1984,第42页。
[22] : Law and : A View of Moral . Press, New York, 2000, p.537.
[23] 唐逸:《西方文化与中世纪神哲学思想》,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2年,第10-11页。
(原载《东南学术》2005年第5期。录入编辑:神秘岛)
主题测试文章,只做测试使用。发布者:佚名,转转请注明出处:https://yufengtangz.com/zhouyi/4267.html